獲獎美國記者芭芭拉·德米克講述了四川阿壩如何成為藏傳佛教徒自焚之都的故事。
作者:馬西莫·英特羅維吉(Massimo Introvig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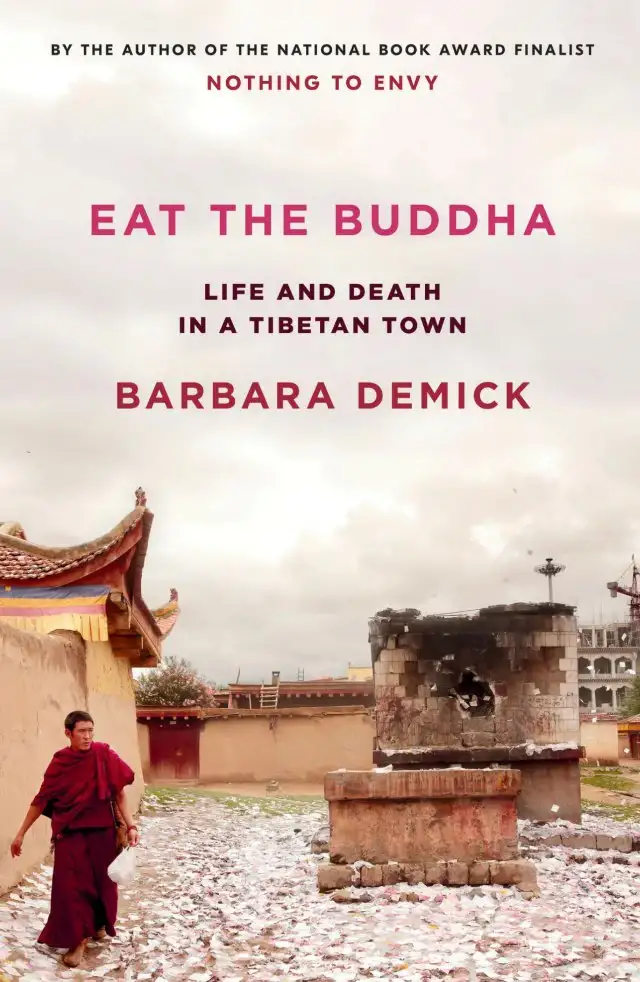
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2009年出的書《我們最幸福》(Nothing to Envy, New York: Random House 紐約:蘭登書屋)是朝鮮政治宣傳最大的噩夢。這名美國記者用其在《洛加維納街》(Logavina Street,Kansas City: Andrews McMeel,堪薩斯城:安德魯斯·麥克梅爾出版社)一書中描繪1996年波斯尼亞首次使用的手法,通過追蹤朝鮮第三大城市清津市(Chŏngjin)幾個居民的日常生活,描繪了一幅朝鮮生活的真實畫面。《我們最幸福》被譽為2009年最令人難忘的一本書,因為德米克在書中講述了普通人經歷的恐怖故事,描繪了飢餓的朝鮮民眾以及瘋狂的政治宣傳不斷地給他們洗腦,試圖讓他們相信朝鮮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若有人嘗試過世界公認的正常生活,都會被判以重刑,甚至會被處死。《我們最幸福》當年榮獲塞繆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現為Baillie Gifford Prize,巴美列·捷福獎)。在英國,該獎項會頒給年度最佳英文非小說類圖書。
德米克在韓國居住六年後,於2007年搬到中國。她對西藏產生了興趣,還去了西藏,儘管外國記者在西藏自治區進行大量的實地考察非常困難,而且還受到很多限制。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只佔西藏歷史面積的一半,另一半則分散在中國的四川、青海、甘肅和雲南等省份,現已成為多數藏人的居住地。西藏自治區以外的青藏高原地區還是現任達賴喇嘛等多位西藏領袖人物的誕生地。
最近的幾年前,西方記者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區走動要比在西藏走動相對容易一些。因此,德米克決定研究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一百萬人口)阿壩縣(七萬三千人口)的縣城阿壩鎮(一萬五千縣城人口)。
阿壩曾是古代半獨立麥桑王國的都城,雖然西藏和中國都聲稱對該地區擁有主權,但事實上當地一個王國曾長期獨立統治著該區域。德米克筆下的一名主人公貢布公主是麥桑王國末代國王的女兒。她於1950年生於阿壩的皇宮,見證了麥桑王國在中共軍隊到達後如何走向終結。1958年,國王被迫退位。雖然他和妻子起初就對中共持妥協立場,但他們在文革期間都「失蹤」了。也許,王后是被人殺害的,而國王則是自殺。當時,貢布公主在北京一所中共高幹子弟學校讀書,正準備成為一名忠誠的愛國者。在文革期間,貢布公主因其階級出身而被滋擾,隨後被發配到新疆的一個國有農場。後來她得到平反,1989年獲准前往印度。之後她留在了達蘭薩拉,與藏族社群一起,再也沒有回過中國。
貢布公主對阿壩的人都很熟悉,包括著名的格爾登寺的喇嘛。德米克通過1958年的西藏災難,講述了城裡其他藏人的故事。當時,中共在西藏強推「民主改革」,通過集體化徹底破壞了當地的經濟,並通過無神論宣傳、對僧侶的騷擾,加上隨後文革的恐怖事件,徹底摧毀了古老的藏傳佛教文化。德米克書中的幾位主人公對很多細節都記憶猶新。

在德米克開始她的研究項目之際,阿壩因為別的事開始被世界所知。2009年2月27日,格爾登寺年輕僧侶洛桑扎西(暱稱:扎白)以自焚的形式抗議中共對2008年青藏高原地區維權遊行示威的鎮壓行動。扎白本想效仿佛教史上曾由於不同原因自焚進行抗議的著名僧侶,但他不太清楚具體該怎麼自焚。他被警察從死亡線上救回,後來出現在中共的宣傳視頻裡。據德米克說,扎白當時還打著麻藥,他「供認」自己被格爾登寺其他僧侶的「操縱」才那麼做的。
但是,在一份長長的名單上,扎白只是第一位自焚者。截至德米克完成該書時,已有156名藏人自焚(現在已有165名)。大約三分之一的自焚者來自阿壩及其周邊地區,阿壩也因此成為人們所熟知的「世界自焚之都」。很多自焚者是僧侶,他們的自焚也越來越有技巧,通過事先喝下汽油讓身體也從裡面燃燒來確保自己不會被救活。

德米克的書並不是關於西藏自焚的學術性作品。《藏學研究》(Revue d’Etudes Tibetaines)的一期特刊在宗教、文化、政治等層面上對自焚進行了探討(英文),還收錄了2012年在巴黎法蘭西公學院(Le College de France)舉行的一次研討會的會議記錄。值得讚賞的是,該期刊通過「數字喜馬拉雅」項目提供了這一重要議題的免費下載。毫不意外的是,讀者會發現關於自焚仍存在諸多爭議,包括達賴喇嘛對自焚的態度和佛教對這些事件的神學立場。達賴喇嘛不提倡這種行為,但對自焚者的勇氣表示欽佩。多個佛教派別都有著關於自焚的悠久傳統。很多人還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通過自焚抗議時任總統吳廷琰(Ngo Đinh Diệm, 1901-1963年)的越南僧侶們。
德米克順帶提到了這些爭議的內容,但她對講述一些自焚者和他們朋友的個人故事更感興趣。為什麼他們要自焚?為什麼多在阿壩?他們實現了什麼目標?這位記者認為自焚源自宗教意義上的盼望和自身的絕望。一方面,自焚者相信這種只傷及他們本人不傷及他人的非暴力行為可以改變世界,另一方面,他們感到其他所有的抗議途徑都被堵死了。
阿壩成為這些抗議事件的中心,因為在藏人聚居地當中,阿壩第一個經歷了中共軍隊大規模的破壞。上世紀30年代共軍首次侵擾這一地區時,飢腸轆轆的紅軍士兵烹煮並吃掉了寺廟裡聖鼓的鼓皮。當他們發現寺裡的朵瑪(佛教小塑像)是由青稞面和酥油製成之後,也吃掉了它們(這也是書名《噬佛》的由來)。他們還摧毀了珍貴的經書並殺害了寺裡的僧侶,這些事情都發生在1958年運動和文革之前。1958年,有些人認為武裝抗爭是一個選擇,但現在他們的後代已不再存有這樣的幻想,幾十年的苦難和暴行催生出了自焚。
這些自焚者達到什麼目標了嗎?他們使得外國人(包括記者)進阿壩的難度更大了。德米克聲稱,目前有五萬名中國安全人員監視這座有一萬五千縣城人口和七萬三千全縣人口的小城。德米克認為,自焚造成的國際窘境的確收到了一些好的成效。阿壩縣的漢族流動人口逐漸減少,幾個將使阿曲河乾涸的河流改道計劃也已被取消。據當地人說,如果實施這些計劃將會造成巨大的生態災難。
另外,對藏人身分和文化認同的鎮壓遠沒打算停止。2020年3月,阿壩第三小學由藏語教學改為漢語教學。2019年,所有學校的學生被要求參加一個旨在要求他們「表達對中共無限熱愛」的音樂大賽。
總而言之,阿壩縣並不比朝鮮好,正如德米克所總結,「藏人的恐懼程度,與我在朝鮮所看見的不相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