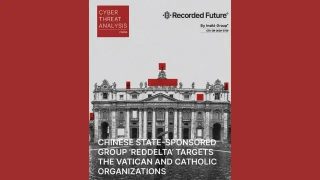《亞洲新聞》一篇報道對2018年梵中協議的「成本-效益」進行了大膽分析,讓人們想起拿破侖企圖掌控教會的前車之鑑。

馬可·萊斯賓蒂(Marco Respinti)
中國前總理周恩來(1898-1976年)有一句名言。1972年2月,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 1913-1994年)歷史性訪華期間,周恩來被問及如何看待法國大革命所產生的影響,他回答說「下結論還為時尚早」。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都普遍認為周恩來這句話指的是於1789年爆發並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法國大革命。後來,那次中美領導人會晤時一同在場的美國外交官傅立民(Charles W. “Chas” Freeman Jr.)指出,其實周恩來當時指的是法國1968年那場騷亂。但無論周恩來指的是這兩者中的哪次事件,他說的都沒有錯。即便是今天,要評價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運動所造成的破壞與後果都仍「為時尚早」(很有意思的是,「五月風暴」中很多人自稱為毛主義者);而法國大革命首開政治革命的先河,就連共產主義革命也與此密切相關。所以,要說法國大革命什麼時候會失去影響力——如果這一天會到來的話——也為時尚早。
200年前法國的反天主教思想
共產主義的鼻祖卡爾·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年,德國人)非常熱衷研究法國大革命。他曾嚴厲地批判法國大革命,稱其為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儘管如此,他仍非常感謝法國資產階級,因為大革命前的法國是由天主教會和當權貴族在某種程度上形成「友好」同盟所共同維持的以天主教為基礎的社會結構,而法國資產階級在竭力推翻這個「舊制度」中起到了關鍵作用。馬克思很清楚,法國大革命應是一個需要幾個世紀來逐步推進的過程,而「急功近利」注定使革命失敗。就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出現了早期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驅,包括格拉克斯·巴貝夫(Francois-Noel “Gracchus” Babeuf, 1760-1797年)和記者雅克·埃貝爾(Jacques-Rene Hebert, 1757-1794年),只是他們生不逢時,很多年後,他們所幻想的集體主義社會才在世界多地日漸發展成熟,而他們當初則抱著幻想被法國恐怖主義分子送上了斷頭台。恐怖主義分子是大革命期間暴力行為達到高潮時,主要革命黨派對施行恐怖統治的激進派的稱呼,而那兩位共產主義先驅卻一邊對他們表示讚賞,一邊批評他們仍不夠激進。
兩個世紀前爆發的這場法國大革命開創了現代國家制度。大革命的構想今天來看無疑是過時的,但革命時期的法國是首個嘗試全面實施極權主義並且取得成功的國家。革命時期的法國是歷史上第一個極權國家,也是第一個實施種族滅絕的國家(隨後我會再談這個問題)。
當革命政府的統治血腥、荒謬到極點時,法國各地整個社會都起來反抗。1793年,全國曾一度有60%的地區起來共同武裝反抗巴黎的中央革命政府。其中最出名的叛亂發生在法國西北海岸被歷史學家稱為「軍事旺代」的地區,該地區比原本的旺代省(叛亂的發源地)要大得多。
從本質上說,旺代叛亂是天主教徒為了捍衛信教權利對極權政府的一次反抗。
巴黎的革命政府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實施了一系列毀滅性的反天主教措施,其中包括修道院國有化,沒收教會財產,攻擊修士修女,打壓宗教團體,屠殺信徒、神職人員以及殘疾人和窮人(1792年發生的著名的「九月屠殺」可與1939年至1941年期間德國納粹對殘疾人實施安樂死的T-4行動相提並論)。極權統治達到高峰時,法國革命政府強迫天主教教士宣誓效忠政府,這意味著他們必須在宗教問題等各方面服從政府;在巴黎,他們還戲劇性地把路易十六(1754-1793年)送上了斷頭台。事實上,對這位波旁王朝國王的處決被渲染成是對神權的嚴重打擊:因為不可能直接攻擊天主本身,所以那些革命黨就試圖攻擊神權在地上的「代表」,即國王與教宗。
實際上,自中世紀盛期以來,法國人民對君權神授一直深信不疑,認為國王代表天主行使政治權力,以捍衛自由、正義、仁愛以及宗教信仰。但法國革命黨卻希望儘快取消羅馬教皇的職權,他們將教宗庇護六世(Pope Pius VI, 1717-1799年)驅逐,後將其俘虜至法國,一直關押到1799年8月29日逝於瓦朗斯。之後,精明的拿破侖·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年)悄然成為法國大革命成果真正的繼承人,並驅逐教宗庇護七世(1742-1823年),直到這位法國暴君在幾次重要戰役中戰敗後,庇護七世才得以自由。
永遠不要反對政府
1972年周恩來所說的那句被誤解的話並不是法國大革命與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之間唯一的聯繫。2018年梵中協議表明了兩者之間更密切的聯繫。至少,來自中國北方的學者李若翰(化名)是這樣認為的。他將這份臨時協議與拿破侖同庇護七世簽署的《政教協定》進行了對比,發現兩者驚人地相似。李先生撰文闡述了他的觀點,並在《亞洲新聞》(AsiaNews)上以英文、中文、西語、意語四種語言發表。《亞洲新聞》是宗座外方傳教會官方通訊社,主編貝爾納多.切爾韋萊拉神父(Father Bernardo Cervellera)被公認是研究中國天主教問題的傑出專家。
在詳細介紹了法國大革命殘酷又蠻不講理的反天主教政策後,李若翰意味深長地將話題指向了法國企圖控制教會的重大變革在實踐中是如何徹底失敗的。他寫道:「1790年7月12日革命黨人頒布的《神職公民組織法案》核心條款包括:第一,重新劃分法國的教區。在大革命之前法國擁有134個教區,大革命時期透過這個革命法案宣布將合併天主教教區。將原有教區按照法國行政區域重新劃分合併,合併之後變成51個教區。第二,主教自選自聖。法國將設立一個首席主教,所有的主教都要從法蘭西的首席主教中領受聖職。主教將由教區神職選舉產生,主教的選舉由神職人員和地方代表進行,平信徒可以參與主教的選舉。第三,法國的首席主教由法國政府提名,不再由教宗任命。第四,非常重要的是法蘭西境內所有神職人員包括主教和神父必須要宣發一個誓言,叫『忠誠誓言』。只有在宣發這個誓言之後,法國的神職才可以公開履行職務,拒絕宣發誓言者當處於非法狀態,將不被法國國家所認可。他們將是革命的敵人,將要接受法律的懲處。」
李若翰繼續寫道:「當時法國有131位主教,134個教區,三個教區主教空缺。」然而,「131位主教中只有四位主教簽字,四位主教當中又有兩位是已經還俗的人士」,其中包括夏爾·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 1754-1838年),他「後來被法國革命政府任命為首席主教,主持了一系列的祝聖事件」。而底層的神職人員中,「法國大約十萬名司鐸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宣誓加入了公民誓約,但是還有三分之二的神職拒絕加入,這批人形成了非宣誓派。」最終的結果是,「法國的信友開始離開教堂,他們拒絕從宣誓的神職手中領受聖事。而那些拒絕宣誓的神職則轉而走入了法國的鄉間,他們在教友家中祕密地舉行彌撒聖事,形成了法國非宣誓派的神職。」
天主教徒為保護遭受殘酷迫害的拒宣誓派教士們,最終在旺代揭竿而起。這次起義是為了信仰自由而戰,貴族們也積極地站在這些農民一邊。他們自豪地把念珠掛在脖子上,胸前有耶穌聖心的畫像,這成了他們統一的服飾。當時,革命政府又在做什麼呢?政府下令「摧毀旺代」,對旺代起義軍趕盡殺絕,將宗教與自由從那片土地上徹底扼殺,不留蛛絲馬跡,同時給所有法國人一個教訓:永遠不要反對政府,否則就要付出種族滅絕的代價。革命黨用褻瀆性的「世俗儀式」處死了成千上萬人,修士修女則首當其衝。被殺害的人中還有婦女和兒童,其中,孩童因未來可能會成為反叛者而被定罪,婦女被判處有罪就是因為她們生育了未來的反叛者。旺代大屠殺從1793年下半年開始,直到同年12月旺代起義軍戰敗後仍又持續了半年之久。
如此協議,真的值嗎?
李若翰在他的文章中不忘提及當時的法國教會分裂成了兩派。一派是由政府成立的官方教會,無論是從與信徒的親密程度還是從信徒的人數來講,這些教會都非常不受歡迎;另一派則是忠於教宗的地下教會,儘管他們遭到騷擾和迫害,卻受到民眾的愛戴和擁護。兩派教會之間激烈的衝突和分裂一直持續到1801年。當年,拿破侖認為若再不解決這種局面,他要絕對控制法國人民的精神和思想的美夢就要破滅。
因此,拿破侖這個暴君主動提出要解決這個問題。他向聖座提出一份協定——1801年7月15日,雙方在巴黎簽署了該協定。李若翰解釋道:「在這份協定中,法國政府承認羅馬天主教是法國絕大多數民眾所信仰的宗教;天主教與法蘭西民族歷史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在法國歷史上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是法蘭西多數民眾信仰的宗教,理應可以自由地實踐和信仰。」
然後,這位中國學者說:「這一點,看起來很好,似乎恢復了法國教會的自由。但是,隨之而來的是政府要求教廷重新劃分教區。在大革命爆發的時候,法國的134個教區被強行重新劃分,教廷始終沒有承認法國政府單方面的舉動。但是與拿破侖簽訂的《政教協定》中,教廷被迫作出了讓步,對於法國的教區重新進行規劃,與法國的行政區域合併,並且建立了一些新教區。由原來的134個教區變成了60個教區,其中10個為總主教區。一切法蘭西的主教,不管是昔日發過誓的官方教會的主教還是拒絕發誓的非官方教會的主教,必須要全部退職。法國的國家元首,就是拿破侖,有權力提名主教,但是卻要教宗賦予神權。對於主教的人選,用時下最流行的話就是政治上靠得住為首要條件。法蘭西的一切神職人員,不管是主教還是司鐸都要發一個忠誠於國家的誓言。教會也聲明放棄大革命以來被沒收的教產。作為對教會損失的補償,法國政府將要承擔法國神職人員的生活費用,為他們提供薪水補助。主教必須和當地政府合作,進行教區和堂區的重新劃分。」
歸根結底,聖座未能達成所願,而是拿破侖大獲全勝。拿破侖總是一次次取得勝利:他曾戰敗,又被趕下王位,之後還被流放,但他都能捲土重來,甚至死後靈柩還被重新迎回巴黎。實際上,正如馬克思晚年所料,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國人的反天主教革命激情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並且日漸高漲,逐步向左翼思想傾斜,梵蒂岡與法國後來又多次簽署政教協定,但無一例外都是以拿破侖與庇護七世簽署的這份政教協定為模板。在拿破侖模式的啟發下,很多國家的共產主義政權也屢次嘗試使本國的天主教會與聖座脫離關係,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和我們這裡說到的中國,二者只是分離程度不同,手段則都是軟硬兼施,隨機應變。
那兩百年前的天主教會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嗎?現在回頭看,所有錯誤的決定都變得一目了然,但這也不過是事後諸葛亮。至於中國的問題,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但是這裡還有一個事實和一個問題。事實上,如果天主教會變成了少數群體,並且是受到迫害的少數群體,那聖座就當以保護信徒為首要職責,哪怕這意味著其本身不得不咬緊牙關勇敢面對。雖然有些人願意為此殉道,但是他們不能強求別人殉道。而所說的問題即李若翰對當今的梵中協議所提出的問題:「教廷是否有信心不會重蹈覆轍,讓這歷史的悲劇重新上演?」其實,中國政府每天鎮壓宗教的實際行動都是它對這個問題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