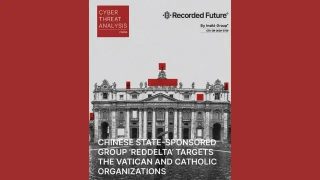17世紀初,天主教會產生了關於基督教信仰與中國儀式的爭論,這是中國基督教史上最重要的爭論,其影響力一直持續到今天。當初,耶穌會傳教士提出了一種適應中國的新的傳道方式。他們主張剛皈依的天主教徒可以祭祖敬孔,因為這些只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禮俗,不屬於宗教儀式。同樣,叩拜皇帝是政治儀式,新皈依的教徒也可以參加。耶穌會傳教士還提倡基督教術語漢譯創新,並且提議淡化十字架的象徵意義,因為中國人並不能完全理解。這種對天主教的「中國化」遭到了一些最古老的天主教修道會的反對和抵制,特別是方濟各會(Franciscans)和道明會(Dominicans),他們表示耶穌會的這種做法是對基督教的背叛並且會最終導致綜攝現象。
這場關於中國儀式的爭論持續了一個世紀,最終以梵蒂岡決定反對耶穌會傳教士的做法而結束。但這個話題至今仍然引發不少爭論。耶穌會觀點的支持派認為,只有將天主教「中國化」,天主教才有可能成為中國的主要宗教。而反對派至今仍然認為,耶穌會提出的天主教「中國化」實際上是一種危險的融合主義。其實,這類問題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當今中國,儀式問題對於中國的基督教仍然具有現實意義。「為了貼近中國人的生活並吸引他們,基督教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適應中國文化」,這個問題與其他問題如出一轍,只不過「中國人」這個詞被換成「非洲人」、「美洲原住民」,又或是「21世紀的人」。

那時,有許多人都認為這一爭論不僅僅對中國很重要,對其他國家也意義重大。《墨西哥歷史》雜誌(Historia Mexicana)2018年7月1日發行的第269期中發表了一篇由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Colegio de México)何塞·安東尼奧·塞爾韋拉教授(José Antonio Cervera)和哥斯達黎加大學(Universidad de Costa Rica)理查德·馬丁·艾斯奇弗教授(Ricardo Martínez Esquivel)合著的重要文章,標題為《中國和歐洲之間的普埃布拉德洛斯恩哲萊斯——帕拉克斯和關於中國儀式的爭議》(「Puebla de Los Ángeles entre China y Europa. Palafox en las controversias de los ritos chinos」,第68卷,頁245~284)。文章討論了墨西哥普埃布拉的天主教主教胡安·德·帕拉克斯(Juan de Palafox,1600-1659)介入中國儀式爭論一事。帕拉克斯是一位非常有名且頗具影響力的主教,他遠在墨西哥都能介入此事,足見儀式問題對全球的影響力。《寒冬》此次的採訪嘉賓就是該文章的作者之一,理查德·馬丁·艾斯奇弗教授。
「中國儀式」問題對中國的基督教歷史至關重要,您能為我們總結一下嗎?
無論是在中國的教會、護教學界還是在學術界,「中國禮儀」之爭直到今天都是辯題。這個爭議對於中國基督教具有決定性意義,同時也影響了耶穌會的命運,以及天主教會17世紀以後向不同習俗地區傳道的走向。從20世紀開始,有關這個問題的辯論就不僅僅局限於神學領域,而是擴展到了學術領域。
爭議主要圍繞三方面問題,一是如何在漢語中建立或創造一套傳道時會使用的關於救贖和末世的基本術語,二是該如何對待中國的祭祖敬孔儀式,三是基督徒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參與被認為是中國式的異教活動。三個不同地區的傳教士與其他修道會的成員,中國人(從國家、地區以及個人層面),以及和梵蒂岡討論了這三個方面。
在短短幾年之內,這場爭論從一開始的僅限於在中國的傳教士之間的私下談話,擴展到教會的教學場所、大學,以及歐洲和美洲出版的書籍和論文,從而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全球思想運動。自此,從北京、廣州、羅馬、巴黎、里斯本、薩拉曼卡和馬德里,到新西班牙的普埃布拉德洛斯恩哲萊斯都展開了關於「中國儀式」的辯論。
在您與塞爾韋拉教授合著的文章中,您指出儀式問題與另外兩個問題密不可分,一個是因為很難向中國人解釋清楚主耶穌釘十字架的事,所以在向他們傳教時是否可以少提十字架以及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話題;另一個問題是如何把基督教術語翻譯成中文。我們先從主耶穌釘十字架說起,這個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兒呢?
十字架標誌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話題。中國人不能理解為什麼上帝曾經被釘死。另外,在一個順服執政掌權大過一切的國家裡,百姓很難理解既然釘十字架是當時執政者實施的懲罰,那為什麼還要紀念主耶穌被釘十字架。方濟各會和道明會的修士抵達中國後,指責耶穌會士幾乎不提十字架,鑒於此,這兩個修會的修士特別注重傳講基督教的標誌——十字架,特別是他們在中國的前期階段。
那麼翻譯問題又是怎麼回事呢?
大體上有兩種方法可以創建傳道必備概念的漢語術語:第一種是音譯法,即根據術語的歐洲語言發音產生其漢語譯名;第二種則是從中國文化中的現有術語中找詞,雖然意思上會有細微差別,但都是在基督教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麼,這種跨文化傳教的翻譯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證新造的漢語術語準確傳達該詞在基督教教義中的意思?若根據音譯法造詞,就會導致傳達的教義比較膚淺而且讓人費解,而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詞,有時又會使得翻譯出來的理念和戒律達到適得其反的效果,從而「玷污」基督教。舉個例子,比如對「至聖者」的稱呼一開始是通過音譯法造詞,但最終還是漢語中與這一概念相似的詞被普遍認為效果更好。公元1604年,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的《天主實義》一書出版,他在書中提到「上帝」「天」和「天主」這三個詞的意思是對等的。第一個詞「上帝」這一說法產生於商朝(1766-1122),而利瑪竇將儒教中的「上帝」一詞轉指基督教中的「神」。第二個詞「天」讓人感覺至聖者不近人情,這跟基督教的理念截然不同。最好的是第三個詞「天主」,該詞一直沿用至今。不過,後來利瑪竇和其他耶穌會士將這三個詞作為同義詞通用。
然而,基督教所指的「神」的對應詞彙在中國文化中能否適應是由中國社會的語言文化習俗決定的。如果利瑪竇選擇用「上帝」來表達拉丁文的「Deus」(神),那是因為中國人已經在漢語語義領域中建立了神學詞彙的價值。也就是說,無論利瑪竇建議使用的詞最終是成功還是失敗,要使中國理念(特別是儒家理念)基督教化,沒有明朝末期(1368-1644)發生的一些反對基督教的事情是不可能實現的,而「上帝」一詞從原來的意思變成了Deus這樣的語義重構其實在17世紀上半葉引發了許多儒教徒和佛教徒的不滿。換種說法就是,本土能動性是這種跨文化概念植入成功的原因,因為它是一種以大眾為基礎的社會構建,而非像殖民地那樣通過外來勢力強行施加。
您的文章是關於普埃布拉德洛斯恩哲萊斯(即現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市)的主教胡安·德·帕拉克斯,他是如何參與到此次爭議當中的呢?
胡安·德·帕拉福克斯主教帕拉克斯當時寫了兩封信,第一封寫給了西班牙國王腓力四世(Philip IV of Spain,1621-1665),第二封寫給了教皇英諾森十世(Pope Innocent X,1644-1655)。第二封信在帕拉克斯離世幾年後被公布於世,主要在18世紀下半葉由耶穌會的反對者以全篇或在論文中部分引用的形式翻印。
帕拉克斯可能出於執行他的民事和宗教職能而介入此事,或者是由於他與耶穌會的個人衝突——這點在下面的問題中會解釋。帕拉克斯曾是印度皇家議會(Royal Council of the Indies,1633-1653)的成員,擔任過普埃布拉德洛斯恩哲萊斯的主教(1640-1649)和新西班牙總督(1642)。那時,菲律賓都督府隸屬於新西班牙總督轄區,該都督府給了美洲的教會機構參與中國的傳教活動的機會。奧斯定會(Augustinian)、道明會和方濟各會的傳教士在前往東南亞殖民地、中國和日本(或返回歐洲)的路途中參與了中國的傳教活動,他們走的是大西洋至太平洋的越洋路線,第一站在新西班牙停留,由帕拉克斯接待。
然而,帕拉克斯參與該爭議辯論的關鍵事件恰逢該爭議的形成初期,我指的是道明會傳教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1597~1664)和閔明我(Domingo Fernandezde Navarrete,1610-1689)在1646年到1648年待在新西班牙的期間。他們當時是從羅馬出發,打算前往中國,身上帶著第一份羅馬教皇發布的有關禁止使用耶穌會的方法給中國人傳道的法令(1645年)。黎玉范是1633年第一批抵達中國的道明會傳教士之一,十年後他回到了羅馬,並針對耶穌會士提倡的適應策略提出了17項控告。對於閔明我來說,那次是他第一次到中國——禮儀之爭的中心國。在中國的幾年裡,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發表了一些作品,因此成為在17世紀下半葉全球辯論這類爭議的主要人物。
您認為帕拉克斯在給教皇英諾森十世和西班牙國王腓力四世寫的信中呈現的極端反耶穌會主義僅僅是帕拉克斯一段時期的態度,那麼是什麼導致他那段時間如此反對耶穌會呢?
帕拉克斯在擔任普埃布拉德洛斯恩哲萊斯的主教時,因著在政治、經濟和司法方面觀點與耶穌會士不一致,他們之間衝突不斷。例如,在新西班牙,耶穌會拒絕奉獻十分之一,所以帕拉克斯主教就向皇家贊助人,特利騰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和主教轄區上訴,試圖將耶穌會士所服務的農村教區世俗化,撤銷耶穌會士的傳道證,中止他們講道和管理懺悔聖事。
天主教會最終在2011年為帕拉克斯行宣福禮,您對此事是怎麼看的呢?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宣福禮始於1666年,花了將近350年才完成。還有一點也引起人們的注意,帕拉克斯經常被過分地用作反耶穌會的旗幟,而天主教會卻在第一位耶穌會教皇當選的兩年前為他舉行宣福禮。天主教會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天主教會想通過此次宣福禮傳遞什麼信息呢?作為一名歷史學家,以上就是我能想到的問題。至於帕拉克斯是否當得起此宣福禮,這就是一個關乎宗教信仰的問題了,不涉及我所研究的領域。
大體來說,我們今天可以稱帕拉克斯的介入為「中國儀式」爭議全球化的一個標誌。在基督教融入中國文化這一話題仍然存在爭論的今天,這場爭議能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呢?
「中國儀式」這一問題的爭論是全球觀念史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現象歷時悠久,而且在不同大洲的許多區域中出現。
這個話題現在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因為它是辯論和分析宗教信息在其他文化中適應、融合或改編的重要因素。在中國發生的跨文化交流可能會導致(儒家和基督教)在儀式上的混淆,使得耶穌會士不僅僅與其他修道會(方濟各會、道明會等)以及中國的精英人士的想法相抵觸,還與中國皇帝、聖座,最後甚至與中國和歐洲的世俗大眾的想法相抵觸。
綜上所述,鑒於帕拉克斯寫的信在中國、歐洲和新西班牙引起的共鳴以及這些信件在18世紀歐洲的廣泛使用,我認為,從帕拉克斯在17世紀對這些爭議的介入,明顯可以看出一個早期的思想傳播的全球公共領域,或原始全球領域已經建立了。問題已經擺在桌面上,而且無論是從宗教、地域還是政治角度上看,這個問題仍在繼續,甚至加深。